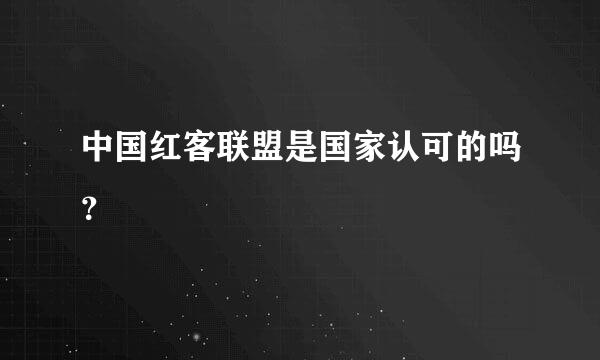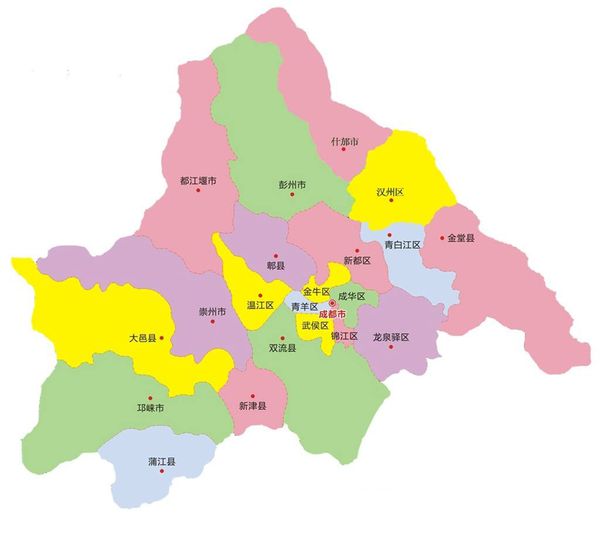刘禹锡在其诗文表赋中,对自己在地方任职多年的人生遭遇反复使用“贬、谪、降、迁” 等语词,后人也多以此作为刘禹锡属于贬官的依据。那么,刘禹锡真的是贬官吗?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刘禹锡在外放连州刺史途中被贬为朗州(下州)司马。虽然由刺史贬为司马,但下州司马秩从五品下,与其在朝廷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秩六品上,官品还高了半级,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还是升了官的。元和十年(815年)七月,白居易贬江州(今江西九江,上州)司马,经过“泪湿青衫”的无奈和不解之后,他怨中寻乐,为文曰:“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1。”即州司马是只领高薪,但不参与地方政事,状若云游野鹤的闲官。“逍遥自在”的背后,是政治地位的边缘化,晾放一隅,则实属贬谪矣。所以,在朗州九年,属于贬官无疑。 后来,即元和十年(815)三月,刘禹锡复授连州(中下州)刺史,秩为正四品下,官品比下州司马高几级,应该说是升了官而不是遭到贬谪。特别是赴任之前,还受到了皇上的亲自召见和勉励,也算是一种难得的荣耀。所以,从州司马升迁为州刺史,久居荒隅的刘禹锡虽然未能位列朝官,毕竟也是独当一面、有一方用武之地的地方主政,政治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升迁。 多年以后,即大和五年(831)十月,刘禹锡以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再度主政地方,再次出为苏州刺史,官至从三品,不再有“贬谪”之论。又因赈灾有功,唐文蠢敬宗给他加赐紫金鱼袋2,服色与正三品朝臣同,则已是同级地方官之极致,他也未说自己是贬官了。 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开元、天宝盛世时期,朝廷对犯了轻罪,不适宜在京城任职的官员,贬至边疆及岭南等荒蛮之地,任地方主官或员外官等闲职,统称为左降官,也叫贬官。犯了重罪的人,则大都流放边疆充军,称为流人。左降官具有一定程度的流放性质,所以过去朝廷的诏令也往往把他们与流人相提并论。直到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四月,刑部上疏朝廷,才对贬官与流人作了概念上的区别:“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流为减死,贬乃降资。量移者却限年数,流放者手握便议归还3。”很明显,贬官(左降官)是行政降级的处罚,流人则是对罪犯刑期的量减。 刘禹锡出任连州刺史,官职升高了,既不是左降官,也不是流人,那他为什么在大量的表、启、诗、赋中,还要大打悲情牌,认为自己是遭到贬黜的呢?我认为这也是刘禹锡贬官心态的流露。 清朝中叶之前,我国古代人口数量发展的进程是十分缓慢的,除了战争和瘟疫因素造成人户数短期内急剧下降外,百年间一般基本维持在同一数量级的水平4。据唐史,元和十五年(820年),全国人户数为“237.5万户,1,576万人5”,虽然史称此人户数未包括岭南及边远地区百余州的人口统计,但这些边远州郡都是地广人稀之所,对总体的评估影响不大。换言之,中唐时期的户口及人数,与盛唐时天宝十三年(754年)记载的906.9万户,5,288万带薯慎人6对比,在长达66年的时间里,人户数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呈急剧下降之势,户数减少670多万户,人口减少3,700多万人,两项数据下降均超过70%,幅度之大,简直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人口是统治的基础,这种随年岁增长颛人户不升反降的状况,说明“安史之乱”(762年)给曾经辉煌的唐室造成的重创,延续时间之长,是史无前例的。刘禹锡的父辈在天宝末年因避乱自洛阳移居江南7,少年时代的刘禹锡,对“安史之乱”后动荡的社会现实耳闻目睹,印象深刻。元和十二年(817年)腊月,当他在连州任上得到平定蔡州之乱的消息时,即赋诗三首,一抒情怀:“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8。”不仅反映了他内心对社会安定的渴望,也反映了他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唐玄宗天宝时期的繁华世界。 唐史载连州元和时“领县三,户五千五百六十三,口三万一千九十四。天宝,户三万二千二百十,口一十四万三千五百三十二9”,元和八年(813年),广东人口密度约6人/平方公里10,按面积推算,当时连州的人口(包括属下三县)估计在5万上下,因此,唐史记载宪宗晚年连州人口仅三万多,是真实的。韩愈贬阳山县时,说“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11”,县城如小村,这般荒凉的景象或可作此注脚。连州作为州治,虽不至如下县阳山的荒芜景况,但州治人口估计也不过三几千人而已。此与当时城区面积已达80平方公里12、繁华无比堪称世界中心的长安相比较,州治环境之陌生冷清,用刘禹锡的生花之笔,也难以形容。况且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连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和多名亲属,都是在永州及柳州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八司马”之一的凌准,贬连州司马后无栖身之处,忧郁成疾,双目失明,元和初竟卒于北山佛寺13。 “伴君如伴虎”,虽然刘禹锡对朝官命运的无常深有体会,但远离京都,政治信息闭塞,基本上失去了参与朝政及升迁入相的机会,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对“愿作枫林叶,随君度洛阳14”的唐代士子而言,更是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灵折磨。受贬之地荒蛮闭塞,文化氛围差,缺乏高层次的友朋交往,缺少同道间的相互唱和,无以立名,可谓寂寞难耐之至。身居州衙,长夜难眠,刘禹锡之感受不谛于贬官,也是可以理解的。京官出任地方,与流贬相类,对文人是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前人评价这是“明升实降”,可谓一语中的。刘禹锡等虽然无贬官之实,却怀抱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贬官心态”,向朝廷、向亲友诉说自己的不幸,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表达对当朝的哀怨。 “左迁穷荒、谪降僻远”,在进退维谷,忍受着莫须有的政治惩罚时,左迁之人也在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唐代在改朝换代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经常大赦天下,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左迁官员随时有“量移”或重掌朝政的机会。最典型的莫如杨炎(727-781年),大历十二年(777),杨炎以吏部侍郎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十四年(779),唐德宗李适即位,经人推荐,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州司马一跃而居宰相位15。不过,仅仅过了两年,建中二年(781年)十月,杨炎再遭诬陷,又被贬为崖州司马,并赐死途中,其仕途之大起大落,令人惊叹! 中国古代饱学之士的贬谪,对中国文学史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屈辱、孤寂、恐惧、自伤的感受,冥冥中似乎又孕育着一点希望,喷薄而出的悲情,造就了大量的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词、歌、赋、论等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后人所称的“迁谪文学”,就思想性和文学性而言,与歌舞升平的歌颂文字是有天壤之别的,故能流传下来,刘禹锡无疑是贬谪文学界中顶级人物之一。
标签:贬官,刘禹锡,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