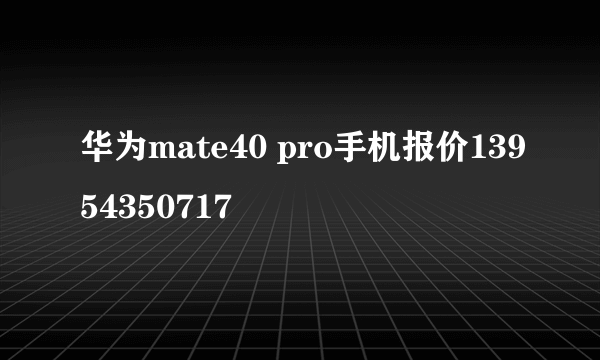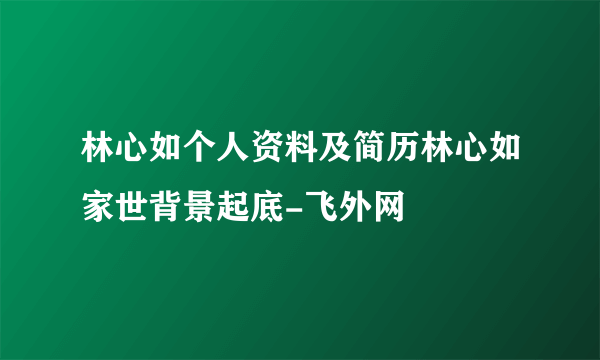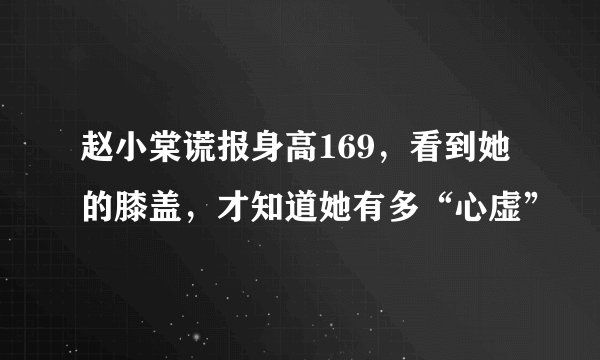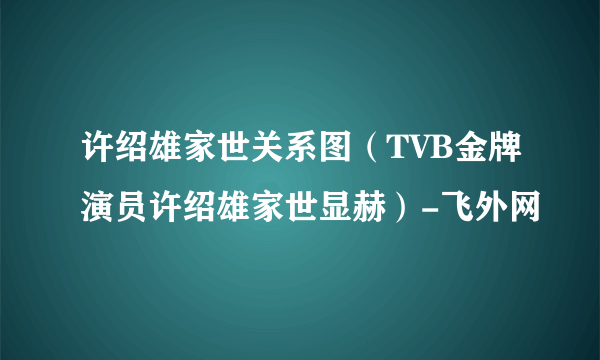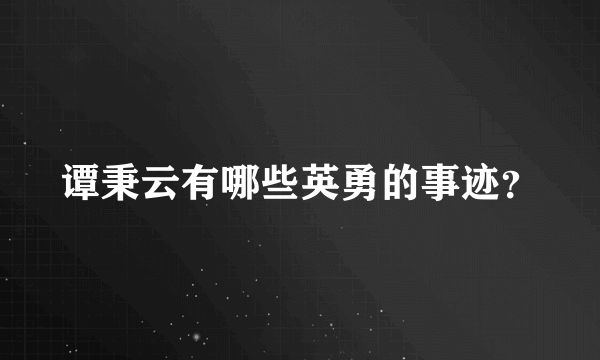
1951年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利用志愿军前突太猛,战线延伸太长的机会,出动大批机械化部队,猖狂北犯,企图与一支已突破志愿军北汉江防线的摩托化部队会合,以斩断江南志愿军后撤之路。
在东京,李奇微将军骄横地向记者宣称,他正在创造一个类似于他的前任麦克阿瑟曾经创造的仁川登陆似的辉煌战例,而这一次吃亏的,不是北朝鲜人,而是中国人。
战局的确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尚在北汉江以南的我军大部队、机关、后勤奉命火速北撤,以免被对方截断。
对方飞机疯狂轰炸,江面上无法搭桥,人多舟少,战士们只好就地砍伐树木,用绳子连成长串横置江面,会水的游向北岸,不会水的则抱着圆木,爬过北汉江。
为确保南岸我军安全渡江,谭秉云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七军某部从东线星夜疾进,赶到金化东南40公里处的390高地,紧急构筑工事,以阻击进犯之敌。他们的任务简单而明白:不惜一切代价,为大部队安全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5月24日这天傍晚,班长谭秉云带着新战士毛和在390高地下面的公路旁边挖好了散兵坑。这地形是谭秉云精心选择的,这一段公路很窄,一边是小河,另一边是山岩。
河岸和岩壁都很陡峭,打坏对方一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很容易被堵塞。作为一班之长,谭秉云深知这次阻击任务的重大意义。
赶到390高地后,他立带领全班战士到指定地点构筑工事。
稍后,他又把其余战士留在山腰上的战壕里打掩护,自己则带着毛和下了公路。谭秉云警惕地注视着公路尽头处的动静。
只见远处的天幕上,掠动着一道道光柱。不一会儿,随着光柱越来越来越近,轰响声也越来越大。有一道光柱穿过前面的一片树林,射到了隐蔽着千军万马的390高地上,再从高地移向河面,又突然移到了谭秉云藏身的地方。
幸亏他早已用树枝将自己隐蔽好,对方看不见他。从树叶的缝隙望出去,光柱一道连着一道,数不清有多少,在公路上不停地晃动,一个个庞然大物从远处疾驰而来。
离远看,尘土冲天的公路上仿佛是扭动着一条巨大的铁锁链,把那一道道光柱也染成了橙黄色。
班长,看清了吗?有多少辆坦克?新战士毛和紧张地问。
还看不清楚,谭秉云从腰间取下一个手雷递给毛和说道,我先上,你在这。这时,从轰响的引擎声
已经分辨得出履带的铿锵声,车上的光柱还直直地射到了隐蔽着班里战友的半山腰上。谭秉云离开用树枝遮挡着的散兵坑,在灌木丛中向前爬去。坦克越来越近了。
谭秉云虽然是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但打坦克比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心中也不免有些紧张。
坦克离他不到20米了,他一动不动;15米了,他直起身单腿跪地,右手紧握着手雷,左手食指套在插圈里,继续耐心地等待着。
坦克每前进一米,毛和与山腰上的战友们心里就揪紧几分。
5米,3米,终于,战友们看见谭秉云手一扬,手雷疾速飞出,成弧线向当头的坦克砸去。
轰!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一团滚烫的气流猛扑到谭秉云脸上。
他定睛一看,吃了他一手雷的坦克并没有被打死,它的前灯被炸烂了,一边胡乱地打炮,一边继续往前爬,很快便从谭秉云面前驶过去了。
谭秉云这一下急了,放它过去,万万不能!他不顾死活地冲上公路,甩开大步猛追坦克,对准它的屁股扔出了第二颗手雷。
他还没来得及卧倒,猛烈的爆炸声中,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额头。眼前一黑,他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公路上。
班长!班长!毛和飞跑上公路,抱住谭秉云大声叫喊。
谭秉云的眼前糊满了额头上淌下的鲜血,热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用衣袖擦着眼睛、额头,焦急地问:坦克呢?坦克呢?
完啦,坦克已经报销了!一听这话,谭秉云才松了口气。
毛和掏出急救包,就往谭秉云头上缠。这时,一串炮弹在他们身边炸开。谭秉云一把推开毛和,急声叫道:快,快打第二辆!打,打!
他提着枪摇摇晃晃地奔下公路,沿着路边的小沟,向迎面逼近的第二辆坦克冲去。这一动弹,鲜血又从扎紧的绷带里渗了出来,顺着脸颊流淌。
谭秉云顾不得抹一下血,靠着还能看见的右眼,将最后一颗手雷向坦克掷去,眼前霎时冲腾起一团巨大的烟火,坦克吱地嘶叫了一声,骤然停下了,但马达还在轰轰地响着,炮口还在喷吐着火光。
谭秉云一个翻身滚到公路上,端起自动步枪向着坦克扫射。他知道此时自己只有主动吸引对方的火力,毛和才有机会靠上前去将坦克收拾掉。
果然,对方转动炮塔,炮弹、机关枪子弹一齐向谭秉云打来。
趁这时候,毛和绕到坦克后面扔出手雷,将坦克炸毁。
谭秉云跑上公路,看见后面的一长串坦克正拼命倒车逃跑。
这时,毛和突然惊叫起来:班长,人!人!
谭秉云蓦地回头,看见从已被炸毁的第二辆坦克顶部钻出来一个美国兵。
这家伙真是奇怪,双手下垂,脑袋顾耷拉在胸前,身子却还在蠕动。
谭秉云一眼便识破了对方的障眼法,这分明是坦克里的美军顶出来的一具死尸。
谭秉云没等尸体落下来,一把抓住坦克上的凹形铁环登了上去。尸体刚从他身边滑落下来,他端起自动步枪,顺着炮塔顶上的天门盖往里送进去,嗒嗒嗒嗒便是一梭子。坦克里发出几声哀嚎,随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谭秉云站在坦克上向南望去,美军的其他坦克巳经跑得老远了。
他回到散兵坑里,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时,才感觉到脑袋重得像磨盘,里面好像有无数的蚂蚁在爬,在咬,伸手抹抹脸,满手是粘稠的血。绷带已经没有了,什么时候掉的,他全然不知。
毛和单腿跪地,再一次将班长头上的伤口包扎好。
天已经放亮了,一轮红日从高高雪岳山后露出脸来。美机开始对390高地进行狂轰滥炸,山头上碎石泥块飞溅,浓浓的硝烟尘土铺天盖地笼罩了公路。
毛和已经被谭秉云派回去要手雷去了,这段与对方最近的公路上只有谭秉云一个人。
这时,一辆篷吉普车从北面疾驰而来,吉普车不断地鸣响着喇叭,好像是叫喊被谭秉云打死的坦克让开道。
谭秉云见车身上涂着醒目的白星徽,驾驶员穿着暗绿色的美军制服,戴着刚盔,估计这一定是前两天突破我军防线的联合国军,企图与这支进攻的装甲部队联络。
他睁着一只露在绷带外面的眼睛,端起自动步枪,瞄准汽车狠狠地打了一个快放。方向盘前面的玻璃碎了,驾驶员猛地歪倒在座位上。
刚才汽车不断地鸣喇叭,倒把谭秉云提醒了,眼下这段公路已经被堵塞住了,其余的坦克不会轻易进到这里,要收拾它们,必须到前面去截击。
于是,他走上公路,向南而去。走了大约100多米,他看中了路边一处地形。
这里,一边是山岩,一边是陡坡,陡坡接近路面的地方长着一笼笼密密簇簇的野葡萄,躲在葡面,既能隐蔽,又能观察到南面公路上的动静。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转身回到了原来的散兵坑。
正巧,毛和带着手雷回来了。
不一会儿,排长也从阵地上下来,隔着老远便大声嚷;谭秉云,毛和说你挂彩了,你快下去,我派别人来换你。
不碍事的,我能坚持。排长,我已经打出窍门来了,手雷往屁股上砸,没一个瞎的。
不行,谭秉云,我看你伤得不轻,还是快下去。
排长见谭秉云头上的绷带血糊糊的,很替他担心。
谭秉云对毛和发脾气:你这小家伙,我叫你去领手雷,怎么告我的状?
毛和也劝他:班长,你下去吧,打坦克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你们这是咋搞起的嘛?我不就擦破了一点皮,有啥子关系?谭秉云使劲摇晃了一下脑袋,表示他伤得真地不重。
排长见谭秉云执意不下火线,只好勉强地点点头,叮嘱他几句,往阵地上去了。
排长一走,谭秉云对毛和说:我到前边去埋伏,你留在这里警戒北边。
毛和往北一看,叫道:班长,怎么又多了辆汽车?
谭秉云说:你叫啥子,那是辆死东西。
没有掩体,没有堑壕,没有一门火炮支援,谭秉云趴在野葡萄丛里,双眼注视着公路前方。
他一个人,一支枪,3颗手雷,将要对付的是美军的重坦克群!这绝对让人难以置信,而又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谭秉云的心里很实在,他估计对方不容易发现他,即使被发现了,这里也是一个死角,炮弹、子弹打不着他,想用履带压他也不可能,坦克只要一离开公路,稍不小心,就会顺着陡坡滚下河去。
他感到很困很饿,便拧开水壶,从挎包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吃了起来。
此时,偌大的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硝烟早已散去,太阳斜挂在空中,天空蓝得耀眼。睡意阵阵袭来,扰得他上下眼皮直打架,要能闭上眼睡它一觉就好了。
他以顽强的毅力同伤痛、疲乏进行着斗争,使自己的意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醒。对方的坦克却迟迟没有动静。
太阳升高了,天气异常闷热。谭秉云解开风纪扣,摘下一片野葡萄叶扇着脸。忽然,路面开始了颤抖。他激动起来,对方终于来了!他丢下葡萄叶,将一颗手雷攥在手中。
不一会儿,一串坦克拉开10来米的距离,嘎嘎啦啦地碾了过来。炮声轰鸣,炮筒像伸出壳外的乌龟脖子,左右转动,喷射出一团团火光。
谭秉云扒开葡萄藤,爬到前面的公路边上,拔出手雷上的插销,将手雷向已经从他面前驰过的第一辆坦克的尾部掷去。
当手雷还在空中打滚的时候,谭秉云已经飞快地回到了葡萄丛中。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紧跟着山谷里骤然发出一长串鞭炮般的声响。
谭秉云探头望去,只见对方的坦克浑身冒火,炮弹、子弹在肚子里啪啪地爆炸开了。公路上一片混乱,所有的坦克都拼命地倒车,大炮、机枪无目标地一阵乱射。
美军装甲部队北进的道路被谭秉云成功地堵住了,他那满是鲜血与灰尘的脸上浮现出骄傲地微笑。
一个月后,在志愿军英模大会上,二十七军军长紧握着他的手说:谭秉云呀谭秉云,你这位孤胆英雄,是天下最大的救命菩萨呀!你把美二骑兵师堵住了8个钟头,我们的部队才得以安全地撤过北汉江啊!
谭秉云的英雄故事,上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被绘制成以志愿军英雄人物为主人翁的系列连环画,《反坦克英雄谭秉云》一书,在儿童中广为传颂。
标签:谭秉云,事迹,英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