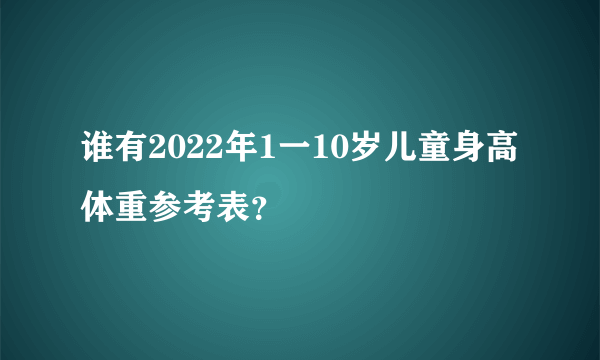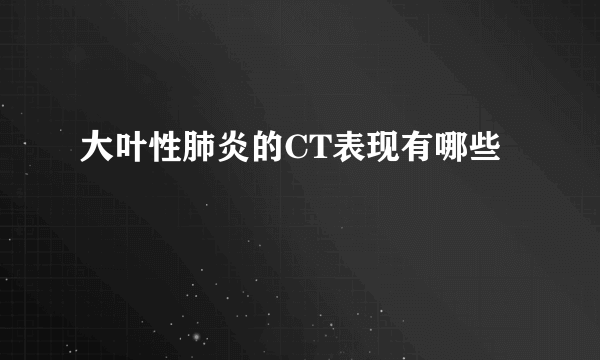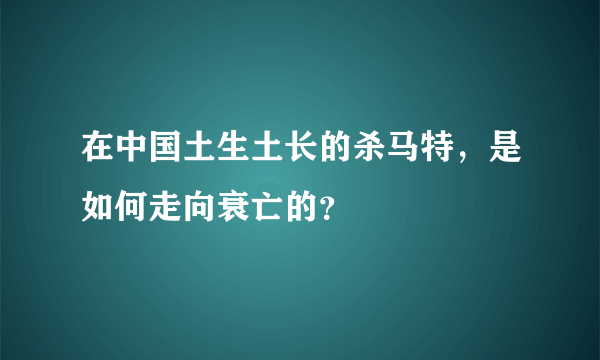
在今年的流行语里面, “爷青回” 三个字注定难以磨灭,随着一次次地疯狂刷屏,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了B站的年度弹幕。
“爷的青春回来了” ,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往往伴随着旧日的光景映入眼帘,熟悉的事物再次来临。
然而,在B站打出“爷青回”弹幕的主力军,并不是倦怠疲劳的中年人,而是正当年的80后、90后,甚至00后们。
尽管他们尚年轻,却开始自嘲心力衰竭,感叹青春易逝,当过去的美好记忆骤然穿越而来时,重逢的惊喜都汇聚在这个词里。
那些记忆的碎片,是蝉声无休无止的夏日,小手拍得通红的水浒卡片,电视里放映的《神奇宝贝》,课堂上抄过的歌词本,街头师傅画的精致小糖人。
明明就那么闪现一下,来如飞花散似烟,而就在恍惚之间,分明看到了栩栩如生与活色生香。
年青一代终究还是沉湎在怀旧的秘境里难以自拔了。
2009年7月16日,芝士回答“魔兽世界吧”,出现了一篇题为“ 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的帖子,正文只有“RT”两个字母,也就是“如题”的意思。
就这样极其简单的一句话,霎时间就爆红华语网络。
7小时内,底下的跟帖就超过了一万,到第三天,电脑回帖数量已经有30多万条,达到上限。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的广告,开餐饮的,学英语的,搞房地产的,都跟上了这波热潮。
贾君鹏究竟是否真有其人,已经不再重要,一场疯狂的创作巨浪就此开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迅速唤醒了一代人的共情。
值得玩味的是,直到2020年,这个帖子下仍有窸窸窣窣的回复,从未间断过。其中自然也不乏“爷青回”这样的表达。
从一度回忆青春,到二度回忆青春,已经过了十多年了。
怀旧情绪的产生自然是复杂的,他不仅有当代青年对世界变化太快,物是人非的怆然和感叹。
另一方面,它还来自于对压抑现实的逃避。
尤其是那些曾经豪情壮志地觉得将来会怎样的年轻人,在被生活不断捶打至扭曲变形,一次次苦苦搏命却又一番番困顿失意后,往往需要寻个角落自我疗伤。
过去的记忆,仿佛就成了一味解药。将无数复杂情绪高度浓缩的“爷青回”,自然就成了打工一族心照不宣的时代暗语。
杀马特青年也许最能体会这种感觉。
在十多年前,最蔚为壮观的一个群体,就是杀马特了。
2020年10月2日,在东莞市石排镇,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 杀马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光听名字就觉得喜感。
这场活动是由罗福兴发起的,这个罗福兴来路不简单,他曾是统领20万的“互联网第一大家族”的族长,“杀家帮”的精神领袖,自封为 “杀马特教父” 。
头衔金光闪闪,号召力理应不差,结果在现实中,罗福兴却碰了个尴尬。
他本来想与国同庆节日,结果被警察叔叔劝住了,只好识趣地放弃。
但又因为活动推迟了一天,就要多住一天酒店,虽然 只是多了几十元的住宿费,却依然让马特们难以承受。
于是,很多人提前打道回府。
结果,在无数QQ群声称盛况空前的杀马特大会, 最后只来了8个人。
“教父?什么屌毛?!”这是几个杀马特对罗福兴的评价。
诚然,这场活动让罗福兴铩羽而归。但也给了我们另一层思考,在急速变幻的工业时代里,城市森林正在吞噬着土地,杀马特这个群体,从未消失过。
2017年,导演李一凡开始拍摄杀马特。 此时,距离杀马特文化鼎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数年。
在纪录片工作开始之前,李一凡就遇到了困难,他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杀马特。
尽管他物色到了各类QQ群,但是里面有很多门槛,比如进群需要杀马特发型验证、火星文沟通等等。
好在,李一凡通过自己的三教九流关系网,找到了“教父”罗福兴,他们约在了一个破旧的小旅馆,开始一场谈话。
这样谈话有些沉闷,因为双方好像不在一个世界。导演想谈 文化抵抗,审美自觉,消费社会景观 ,等等诸如此类学究气的议题。
但罗福兴却只是谈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经历。
李一凡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2017年,他搞到了钱,就和罗福兴说,走吧,带我出去转转,去看杀马特的世界。
结果他发现罗福兴是个宅男,一个现实中的杀马特都不认识。
罗福兴如今身高170,体重只有90多斤,小时候的他更加瘦小。那时,同班同学经常欺负他,没事就揍他玩,用脚踩在罗福兴的手指上,然后转动身体,嘻嘻哈哈。
他向老师求助,老师嫌他成绩太差,把他安排到最后一排,和垃圾桶待在一起。
他想告诉家人,却发现除了母亲没人会理他,就是唯一能说话的母亲,因为忙于打工也常常见不到。
迫于无奈,他找了一把菜刀放在书包里,如果再被欺负,就可以拿出来,但他终究没敢拿出来。
后来的人生道路上,罗福兴仍被懦弱和自卑包围着,而这些里面,还藏着一丝倔强的自尊。
外界的人会以猎奇的视角观察罗福兴,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他出名了。
他被浙江卫视邀请去拍《中国梦想秀》,节目组跟他说好,只聊创业梦想,而到了现场,他才发现, 嘉宾和观众只想看他的笑话 。
于是,现场大屏幕上,罗福兴杀马特时期的自拍被放出来,台下几百个观众哄堂大笑,嘉宾们则不断用专业名词调侃他的“时尚”品味。
罗福兴愤怒了,转身奔出舞台,大手一挥,说不录了。
李一凡打动罗福兴的地方,是他对罗福兴说,我就想让你们自己来讲讲杀马特是什么。
罗福兴便和李一凡走了,他们用脚步丈量土地,从深圳开始,走遍了广州、惠州、重庆、贵阳、黔西南州、毕节、大理、玉溪等等地方,去见识真正的杀马特们。
在东莞的石排镇,李一凡发现了杀马特聚集最多的地方。
一位紫发的杀马特告诉他,自己刚来到城市,租好了房子,晚上下班了,连房子在哪里都找不到,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房子都一样。
旁边有位“小姐姐”走过来,问他,兄弟你在干什么,他回答,在找回家的路。小姐姐就告诉他怎么走,走到一半,问他借钱,说一两千就够,领到工资就还。
紫发杀马特信以为真,把钱给了她,最后等了四五个月,也没等来还钱,留下的联系方式都是假的。
很多出来打工的少年都有类似的经历,刚下火车,行李就被人拎走了。
在偌大的城市中,这些少年感到的是无助和绝望,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根本无处伸冤。
杀马特少年们,在曾是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集体失位。他们十来岁的年纪,就被迫和社会硬生生摩擦,靠着自己独立支撑下来。
罗福兴说,头发会给人勇气,从形象上说,有一种可以震慑人的东西。而在大家的印象中,这就是坏孩子,坏孩子是不会受欺负的。
这几乎所有杀马特精神自卫手段—— 只要造型足够夸张,就没人敢欺负自己。
来城市打工的杀马特们,从小缺乏关怀和陪伴。当他们和老乡被分配到工厂后,工厂会把他们化整为零,安排到不同部门,以防闹事。
这些十四五岁的少年,精力正旺盛,而社交却约等于无,苦闷需要排解出去。
领了工资,就成群结队去溜冰场溜两圈,去迪厅蹦两下,去慢摇吧喝杯酒,去网吧上上网。
没钱的话就一起出去炸街,即便路人的眼光中带着鄙夷,杀马特们也无所谓,至少他们在别的地方,不会有这样的回头率。
现在云南昆明承包工程的“云小帅”,回忆起自己的杀马特岁月, 说那时候只想通过穿着打扮来发泄,让别人感觉自己很独特,哪怕是被骂两句,甚至是吵一架,至少也有人跟自己说话。
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重复机械固定的几个动作,在工位上打瞌睡是常有的事。
机器不会觉得疲倦,流水线上产品容易堆积。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工人们只好用纯柠檬汁提神。
与此同时,步步紧逼车间主任,时刻监督,工人们去趟洗手间都要出示方便条。小作坊还存在安全隐患,轻者出点小疹子,重者则会断手指。
工厂也不欢迎杀马特,因为他们是 叛逆与不受驯服 的象征性。
他们会厌恶工厂,但又想留在城市,这种矛盾时刻鞭打着他们的内心。
罗福兴跟李一凡讲, 他从来不抬头看一栋高楼,因为这些跟他没关系。
随着年纪的增大,技能的匮乏,多数杀马特慢慢回到了老家,而那是一种更为贫乏的生活。
五彩斑斓的头发被剪去,轰隆隆的工厂已经远离,杀马特们又不得不落魄地在家乡面临新的困境。
回首以前的人生经历,他们会觉得荒唐,自己做错了什么,罗福兴总是说,要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
如今,罗福兴把杀马特和工人权益联系在一起,说 杀马特的后退,本质上是工人失去话语权 。
“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玩杀马特,我至少有上升的机会,比如杀马特贵族,至少能让我快乐。”一位杀马特这样说。
与三和大神一样,杀马特少年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何尝不是对阶层固化和社会规训的隐隐嘲讽?
2013年,在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眼里,杀马特无疑被冠上了“脑残”的标签。或是以为这是底层青年通过自我践踏的方式去抵抗主流社会的审美。
当初,李一凡也是认为的,直到他接触真实的杀马特后,才转变看法。
在快手上,我们会见到农村的底层青年,会表演自虐、生吞活蛇、模仿黑社会,这些行为未必和杀马特们没有共通之处。
法国有部纪录片,叫《疯狂的祭司》,讲述当时非洲的桑海人通过跳舞实现被法国殖民者的灵魂占有。
具体来说,是一种附体仪式,通过对白人官员的表演模仿和其他附体的迹象,如口吐白沫、眼球上翻、扭曲的动作,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黑人青年模仿总督、将军、少尉等身份,杀马特少年用奇异的发型装扮自己,前者是希望夺回被欧洲殖民者霸占的统治权力,后者是对某些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的羡慕。
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其实有共通之处。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写过一篇经典论文,名为《企业的性质》。
他着重探讨了“ 雇主与雇员 ”的关系,主人有权亲自或者通过另一个仆人或代理人控制仆人的工作和何时不工作,以及做什么工作和如何去做。
指挥权才是“雇主与雇员”这层法律关系的实质,这种规定是模糊的,解释权在企业家,所以在这个关系内,企业家几乎对员工拥有无限权力,按照科斯的话说,是完全的“主人”。
人们会调侃自己是“码农”、“PTT纺织工”、“Excel女工”,实际正确的称呼应该为“码奴”、“纺织奴”和“Excel奴”。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上映后,85到00后的城市青年群体对这部电影最有共感。这让收到反馈的李一凡感到出乎意料。
同为打工人,他们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压抑。
在“爷青回”的弹幕洪流中,不只是曾经天真烂漫如今汲汲营营的社畜们的青春挽歌,还是他们尝尽了生活苦楚后的一声无奈的自嘲和排解。
于知识青年而言,还能在键盘上敲几个字,喊几声疼。对杀马特们来说,就只能缄口不言了。
乌鸦校尉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
参考资料:·
《杀马特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蓝字计划 《杀马特我爱你》纪录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在贴吧等贾君鹏回家吃饭》Epoch故事小馆 《底层青年的模仿仪式》人民网研究院 《社畜的阶级本质和出路》底层观察家
标签:马特,土生土长,衰亡